我能走进剑桥,既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命运。很早就决定要出国留学,并非国内的高等教育不够好,而是我相信,只有进入一种文化,才能了解一种文化。长久以来,我唯一的目标是美国,托福、GRE、择校、申请,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踏上辽阔的美利坚大陆。而英国剑桥从来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她只存在于我遥远的梦境深处。在我的脑海里,“剑桥”更像一个历史名词,像一顶耀眼而沉重的金冠高悬云端,宗教王权的阴霾,文化传统的厚重,都裹着历史的尘埃。牛顿、拜伦、狄更斯、伍尔夫、达尔文都早已逝去,他们不朽的名字把“剑桥”与平凡隔绝,她成为我梦想中的梦想,从来没料到有一天会变成现实。那年秋天,随着“九一一”的一个晴天霹雳,美国陷入一片恐慌,签证的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英国进入我的视野,剑桥成为我寻梦的地方。
总觉得自己能够徜徉在剑河的柔波里,那是冥冥中和剑桥的一种缘分。最初,我只是抱着嘻嘻哈哈的态度申请剑桥,因为我认定这个说出来都带回音的古老学府跟我这个普通人压根不搭界。有一天,我准备在戴维的电影课后请他帮我写申请剑桥的推荐信。戴维是大学的外教,因我们共同热爱电影而成为好友。他每周开一堂电影选修课,放一部他认为值得一看的艺术影片。那天放的影片叫《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为不同的信仰奔跑的故事。
黑暗中,电影拉开帷幕。我的心猛地一颤,故事里的一位主人公哈罗德竟然是剑桥大学的新生!银幕上,他乘坐老式出租车缓缓驶过1919年剑桥古老的街道。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剑桥的容貌。当时,我并不知道,位于远景的那个尖顶建筑就是国王学院的礼拜堂。我亦不懂,在那街道深处、木门背后,隐藏着剑桥怎样的风神秀骨。我更没想到,那些街道和回廊将成为几个月后我时常经过的地方。看着那些同龄人打着白领结,披着黑学袍,端坐在高大的厅堂里,聆听院长关于荣誉、尊严与传统的宣讲,我被深深地震慑住了。电影里的剑桥离我那么遥远,却又那么富有魅力!我不住地问自己,难道我真地备足了勇气和决心放手一搏么?我真地能够坐在他们坐过的长桌旁,享受他们的光荣,承担他们的责任么?我的肋下隐隐作痛,那里怀揣的正是一份申请剑桥的推荐表。霎那间,这薄薄一页纸竟然变得无比沉重。最后,还是哈罗德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他说,“有梦想就要有胆量去实现。”就是这部电影,就是这句简单的话,给了我追求梦想的强大力量。
申请剑桥确是一件苦差。美国研究生的申请套路循规蹈矩,很快便能驾轻就熟。可剑桥的情形不但与美国迥异,跟英国其他大学亦大相径庭,八百年的历史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剑桥读书的日子是难忘的,各个方面的收获都是巨大的,特别是剑桥的“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让我感触尤深。“举重若轻”是一种风度,是一种气魄,是一种境界;“举轻若重”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两个看似对立的词语,偏偏就能够在剑桥完美地统一,成为剑桥文化传统的精髓。
清朝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苏东坡的诗作时,就说他“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我发现,在剑桥,所有凝重的思考都不凸显其厚重的本质,相反,常常以一种随意、轻松和淡雅的方式呈现出来。
雷打不动的下午茶
初来剑桥,我就发觉剑桥人过得实在滋润,一点儿没有想象中名校苦学的折磨,更不用说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了。剑桥人每天总有大把时间悠闲自在,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下午茶。有时候我恍惚觉得,剑桥就像我们中国的魏晋时代,不管外面是乱世还是盛世,不管天大地大,思想自由永远最大。在这里,不崇尚求同,却希望存异,每个人都要在群体中凸现出自己的个性。剑桥人有个鲜明的特点,喜欢交流,崇尚清谈,恰似魏晋的竹林七贤。而孕育了这清谈之风的正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下午茶。
下午茶是英国贵族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午后三四点钟,女主人用镶金白瓷泡上一壶英国红茶,加入牛奶和白糖,再配上各色点心,招待家人和宾客。这在上了发条的现代大都市已经显得太过奢侈,在剑桥,它却成为师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每天下午,剑桥的大多数学院和系里都会有下午茶供应,而且以学院的下午茶尤为丰盛。铃声一响,红茶、咖啡、热巧克力、饼干、甜点和松饼,都由侍者推着餐车送到大厅。这时候,老师学生就会三三两两地聚拢过来,捧上一杯茶,信手拈来一个话题,天马行空地聊下去。外人要是看到这种情形,大抵都要忍不住摇头,觉得剑桥人不务正业、荒废光阴。然而,只要你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便能真正了解下午茶的深刻内涵。因为剑桥实行学院制,每个学院都是由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学生构成,打破了种族、信仰和专业的局限,让所有人享受真正无边界的交汇融合。就以我自己为例,住在对门的一位化学系的印度小伙子喜欢和我们分享学业上的心得和困惑。我喜欢跟研究德语文学的英国邻居和专攻地理经济学的日本同学切磋厨艺。而更多的朋友是在下午茶的时候熟识起来的,什么学术、论文、旅行、天气、伊拉克战争,天下之事,不论大小,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可别小觑了这下午茶。喝茶不过是形式和手段,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促进多层次的交流,鼓励思想的碰撞,打破观念的局限。这不是上流社会惺惺作态的社交活动,剑桥下午茶的精髓是平等自由的交流。很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伟大作品都是在下午茶的美好时光里酝酿,不少诺贝尔奖得主的伟大发现也是下午茶交流过程中的灵光闪现。想象一下,来自剑桥各个领域的精英在一个下午聚集在一起,喝着茶,吃着点心,轻松愉快地交流着,各种思想在摩擦、在碰撞,不知不觉间美妙的灵感像火花一样闪耀。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个年轻人就是在“鹰”(Eagle)酒吧的闲聊中找到了灵感,并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如果有人问“剑桥的精神”是什么,很容易得到一个莫明其妙的回答:“去喝喝下午茶吧。”所有在剑桥学习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剑桥的精神就弥散在这浓香四溢的下午茶中。自由平等的交流,让人学会表达与分享,谦逊与聆听,尊重与包容。真正的剑桥人有一颗平常的心,每天下午喝红茶、品咖啡,愉快地和朋友聊聊天。也正是他们,可能正在准备即将轰动世界的学术论文,可能明天就正襟危坐在欧盟大会上慷慨陈词。
全英最短的学制
说起剑桥,好像吃喝玩乐说得多,学习钻研讲得少。剑桥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每学期只有短短的八周。第一学期从十月初到十二月初,接着一个多月的圣诞假期;第二学期从一月中到三月中,然后是复活节假期;第三学期从四月中到六月中,主要是在图书馆复习,以及考试,之后就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剑桥真正上课的时间也就前两个学期,区区四个月,全英可谓最短,别看上课的时间不多,可是内容极度浓缩。老师轻描淡写地讲上一个小时,学生如果不花五六个小时课前准备、课后消化,就真的连北都找不到。学习的压力无比巨大,每个学期若不配上一个长假,恐怕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利。
刚到管理系报到时,我拿到的课程表上每学期只排了四五门课,老师居然还说课程有点多,建议慎重选择,可将一门课推迟到下学期再修。要知道,我在北京读本科的时候,每学期密密麻麻地排了十几门课啊!当时,我心中暗想,国外大学果然好混。可上完第一堂课,我的心就沉下去了。课程不多,课时也不多,但课后要做的功课却像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每门课的老师都会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Reading List),每次上课前都有上百页的读书任务。学生可以偷懒不读,老师从来不管。然而,一回不读书,堂课上就像是坐在月球上听天书,那种惶恐与刺激足以成为此后拼命学习的动力。
剑桥的老师自视甚高,把学生亦看得很高。他们默认为,既然这个学生进入了剑桥大学,他就具备了在这个领域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于是乎,老师在课堂上并非简单地教授知识,而是把学生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引导启发大家共同探讨。他绝不会讲解他认为学生应该早知道的东西,因为这既浪费了他的时间,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被鼓励,也被鞭策,把书本上的知识消化并发展成自己的观点,以回应老师抛出的开放式问题。不用举手,不用起立,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断老师,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哪怕是谬论,也是受到赞许的行为。这种授课环境,对于会读书、会思考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学术的天堂;而对于读死书、不动脑子的学生来说,比地狱还可怕。
剑桥每学期就短短八周,每周只有寥寥几堂课,大把时间怎样度过,都由自己做主。想玩乐,每天都有数不清的聚会可以参加;想学习,长长的书单,几十座图书馆,各个学科的开放课程,永远能把时间填满。对于习惯了填鸭式教育的中国学生来说,自由有时候倒真是可怕的东西。就像米兰?昆德拉的一本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学习的自由轻飘飘的,看似没有分量,可是落进每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在一个晴朗的春日,约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聊聊某一篇我们都喜欢的奇文佳作,然后在莫德琳路上好好享用一顿美味的午餐,当然少不了巧克力布丁作饭后甜点。吃完之后,到剑河边,喂喂天鹅,看看水仙,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这是对剑桥学习方式最好的注脚。无论功课多么繁重,无论压力多么巨大,要做学问,尤其要做大学问,就必须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乐观和热忱,这就是剑桥人的学习之道和人生理念。
传说一位意大利鞋王,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回答说“我把每个顾客的鞋都当作上帝的鞋来做”。下午茶、泛舟、假期,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异常丰富的活动,剑桥绝对是个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可是,在剑桥读书的日子,我时时感到如履薄冰,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八百年的剑桥,每个地方都有掸不尽的历史,每条规则都有可以追溯的传统。学术上如此,生活中亦如此。
[$pagetag]事事较真的治学态度
剑河边,一片青草,一波碧水,几只野鸭,聊着天,翻着书,看着景,就是一个曼妙无边的下午。这只是剑桥人在享受读书的情怀。一旦真做起学问来,剑桥人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简直吓人。
在剑桥,我学会的第一课就是较真。我们课上课下,最鼓励的就是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这种自由是有前提的,并不意味着想到什么说什么。一旦学生提出新见解,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依据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茫然,就是灵光一闪,哪有什么依据可循?随便说一句话尚且如此,对论文的要求则愈加苛刻,几近古板。头回交论文,自诩为殚精竭虑的得意之作,却被导师批驳得体无完肤。从文章引用,到措辞斟酌,甚至标点符号,圈圈点点纠正的尽是些小错误。当时的我既委屈又不屑,做大事不拘小节,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可剑桥老师偏偏都爱从小处着手,简直是锱铢必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细节的意义所在。在学术领域,当后人查阅前人论著时,前人文章引用的准确性就格外重要。每一个突破性的新观点,每一篇有建树的新文章,都不是空中楼阁,只有前人打下牢固的基石,后人才可能达到新的学术高度。牛顿如是说,“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这样的较真,我慢慢学会了读书。在国内念了十几年的书,一直是引以自豪的好学生,到了剑桥才愕然发觉,原来自己并不懂得读书。从前,老师会划出考试范围和复习重点,我们只需主攻那些条条框框。这一法宝到了剑桥就彻底失效。剑桥没有所谓的重点,只有一颗不断向更深处钻研探究的心。学习往往从一些参考资料开始,当选定论题方向以后,便有更多的书需要阅读,更多的问题等待挖掘。打下坚实的基础,再展开独立的研究。这个过程是艰辛而孤独的,读什么书,如何读,各有各的方式,各有各的结论。
在剑桥读书,就像拥有整片海洋,大海的浩瀚让人惶恐,每个人都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舵手,诚惶诚恐,兢兢业业,永不放弃,才不至于迷失深海,才可能扬帆远航,到达胜利的彼岸。
繁文缛节的学袍制度
剑桥作为“诺贝尔奖的摇篮”一直在积极地鼓励突破与创新,但骨子里却真正承袭了大英帝国的保守与传统。这种传统的观念从剑桥几百年砖墙石路的缝隙间散发出来,无声无息,却主导了这座小城的魂灵。其他大学仅是毕业典礼时需要穿学袍以示庄重,而剑桥师生以此标榜身份。“袍镇之争”由来已久,是剑桥大学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标志,彰显学者不可动摇的独立地位。据说过去学生出学院上街必须外披学袍,不然便作违纪处理。遥想当年清俊学子一袭长袍翩然若仙,穿行在大街小巷之中,是何等风流古雅。现在这一传统虽然废弃,但在大学和学院的某些正式场合,仍沿袭着穿学袍出席的规定。
剑桥的学袍粗看起来都是一水黑色,无甚分别,但实际上却大有讲头。剑桥大学拥有一整套纷繁复杂的学袍体系,简而言之是袍子和袖子越长,身份和地位便越高。如来参加短期交流的访问学者,统一都穿刚及腰的短款学袍;本科生的学袍一般长不过膝;到研究生,袍子就超过膝盖,而且按学位等级逐渐加长。以此类推,学袍的袖子、丝带、帽兜、扣子等部件都会因学院、专业、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繁琐程度令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但遇到一个内行,仅从你的一身行头,就能把你的身家来历说个明白。剑桥城里有几间专门定制学袍的店铺,历史均在百年以上。店员经验丰富,只问几个小问题,就能帮顾客从一排排长袍中找到需要的款式,令人啧啧称奇。
很多人抱怨学袍制度是繁文缛节,但我却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当我披上黑色长袍,背脊就情不自禁挺直了,神情举止自然而然端庄起来,觉得自己不再渺小平凡,我也成了剑桥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份子,分享着牛顿、达尔文、拜伦的荣耀,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剑桥对整个人类的责任。
恪守礼仪的饮食文化
剑桥注重传统的正餐礼仪,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规定,一餐一饭都庄严不可戏谑。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正式晚宴(Formal Hall),每个学院的风格都各不相同。有的学院要求特别严格,有的学院比较宽松。首先是着装,男士西装女宾正装是最基本的要求,很多学院要求本院师生要一律穿学袍,据说早年还要戴假发以示庄严。有一次我和几位朋友结伴去圣约翰学院赴宴,谁也没穿学袍,结果被明察秋毫的厨师长堵在门口,训了半天的话,直到最后有个朋友披了学袍来,他才放行。一些高规格的舞会,着装要求更高,男士穿正式礼服打黑领结,女士必须穿晚装。如果男士穿西装打领带,恐怕连门都进不去。这正好是美女们展示个人风采的良机,许多女孩即使大冬天还穿上露肩的欧式华服,个个打扮得光彩照人。这种场合,民族服装也是经典之选,既庄严考究,又突显民族风情,让人们眼前一亮。我那一身缎面旗袍一穿下楼,立即赢得满堂喝彩,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话题也随即展开。
除了着装,座位安排也有讲究。有的学院就餐座位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有的学院除了院长的位置其他人都是随便坐。开饭前,通常都有一个简短的仪式,有的学院由司仪用拉丁文主持,有的学院由院长致欢迎辞,有的学院还敲锣,反正是各具特色。邀请好友来自己学院参加正式晚宴是剑桥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剑桥社交传统的经典范例。它营造了一种老友欢聚、新友相识的氛围,亦是一个了解英国传统的机会。餐前在客厅,大家举一杯开胃酒,认识的,不认识的,一声“你好”(Hi)就可以加入到谈话中来,一声“抱歉”(Excuse me)就可以礼数周全地退出。对于深谙英国社交文化的人来说,这是自由和享受,但对于来自东方的中国人来说,还需要学习和磨练。
关于正式晚宴,我最鲜活的记忆是和一帮剑桥华人同学去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赴宴。建于1496年的耶稣学院宏大古老,有一整栋楼都是食堂,分作大小不等的数个餐室。当晚就餐用的是较大的一间,室内灯火通明,不但点了蜡烛,屋顶还有烛形明灯。耶稣学院食堂的座位小得可怜,除了学院院士,用餐者坐的都是无靠背的长板凳,而且用餐空间极为狭小,就像是挤在一起吃饭。
刚入座的时候,大家都谈笑风生,突然铃声响起,所有人肃然站立,迎接学院院士入席。院长致辞,宣布开饭。大家这才坐下来,开始吃面包、喝汤。用餐过程井井有条,人人黑袍长袖,举手投足间充满英国人的斯文儒雅。基本吃完的时候,铃声再次响起,我们起立目送院士离席。站在我身旁的一个香港男孩小声说,“注意看最后出去的那个人!”我心怦怦乱跳,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谁会是最后一个,说不定是位世界著名的人物,可千万不能错过。所有院士鱼贯而出,最后那位个子高高的中年男士走到门边,忽然站定,转回身来,伸出右臂,在空中划了一道弧,身子前倾向大家施礼示意。这时我还愣在那里,现场就已经沸腾了,大家拼命地狂喊、欢呼、吹口哨、拍桌子,一派狂欢的景象。朋友笑着说这是学院的传统。不知是谁的生日,一帮人大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很多人打扮得花里胡哨,带着假发,男生头上插着花,脸上涂着胭脂。还有人站到椅子上致祝酒辞,大家又是一阵喧闹。
虽然已经离开剑桥,这段经历一直深深地埋在我心里。剑桥的学生既保持着对传统的尊重,又宣泄着年轻人如火的热情。新与旧,叛逆与传统,看起来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可以这么完美地融合在剑桥的生活中。我想,这就是剑桥大学虽然饱经历史的沧桑,但是依然焕发青春活力的原因吧。
剑桥的“举重若轻”是一种优雅的风度,是一种宽广的气魄,是一种平和稳重的人生境界。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剑桥生活、做学问莫不如此。而剑桥的“举轻若重”是一种严谨的态度,是一种敬业精神,是一种对完美的执着追求。踏踏实实,关注每个细节,尊重历史传统,勇于改革创新。几百年来,剑桥的文化与传统,所苛求的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像一个真正的剑桥人那样思考和生活。
更多英国大学信息,参见英国大学网:http://www.001uk.net









 高考后申请英国留学
高考后申请英国留学 英国留学奖学金申请
英国留学奖学金申请 英国留学硕士申请
英国留学硕士申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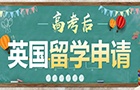 高考后英国留学申请
高考后英国留学申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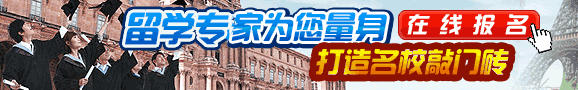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